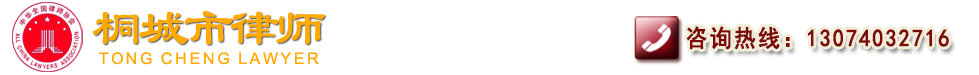合同诈骗罪的形式要件
合同诈骗罪的形式要件-对口头合同可以构成合同诈骗罪的质疑 合同诈骗罪在客观方面的形式要件是什么?是否涵盖口头合同?是目前困惑司法实践的难点,颇为理论界所关注。
就此题目,目前有论者发表了几种意见,概述如下: 第一种意见,以为无论什么形式,只要符合《合同法》划定的合同要件的,其中包括口头合同在内的任何合同,都可以成为合同诈骗罪客观方面的形式要件。
其理论是根据我国《合同法》划定,合同的订立可以采用书面合同,口头合同和其他形式。
[1] 第二种意见,以为根据《刑法》第224条之划定,合同诈骗罪的诈骗行为发生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固然“签订”一词意指书面合同,但“签订”,“履行”属并列关系,在法律并未对履行行为所依据的合同的形式作出划定的情况下,被履行的合同可以是口头合同,也可以是书面合同。
此外,在法条发生竞合时,按照特别法优于普通法的原则,应选择特别法。
[2] 第三种意见,以为口头合统一般不应成为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但口头合同也是《合同法》确认的一种正当形式,假如被告人的诈骗行为发生在经济去来过程中,所利用的口头合同又符合合同诈骗罪之合同要素,且通过签订,履行口头合同过程而骗取财物的,亦应以合同诈骗罪论处,但应从严掌握。
[3] 第四种意见,以为合同诈骗罪中的 “合同”,一般应限于书面合同,利用口头合同达成协议骗取财物一般不构成合同诈骗罪,而应按照普通诈骗罪定罪处罚。
[4] 第五种意见,从合同诈骗罪的客体性质,证据的客观可见性,惩办犯罪最大需要的角度,以为口头合同不应成为合同诈骗罪之“合同”,书面形式的合同理所当然属于合同诈骗罪的“合同”。
[5] 第六种意见,以为按照刑法理论特别法条优于普通法条的原则,合同诈骗罪的形式要件宜界定为书面合同,包括《合同法》第11条对书面合同所作的扩张解释,即信件,数据(包括电报,电传,传真,电子数据交换和电子邮件)等可以有形地表现所载内容的形式,而不包括口头合同形式或者其他形式,否则,难以区分合同诈骗罪与普通诈骗罪。
[6] 回纳上述六种意见,笔者将第一,二种意见称之为扩张说,即将 《合同法》所划定的各种合同,无论从内容到形式全部移植到《刑法》中的合同诈骗罪里来,作为界定合同诈骗罪中之“合同”的参照依据。
第三,四种意见可以称之为有限扩张说,只是程度不同而已。
该说并不否认在一般情况下,合同诈骗罪的形式要件为书面合同,但也不排除在特殊情况下,口头合同也可以成为合同诈骗罪的形式要件。
第五,六种意见可以称之为限制说,即以为合同诈骗罪的形式要件只能是书面合同,排除了口头合同这一形式。
上述观点孰是孰非,本文略作一探讨。
从表面上望,本文探讨的是口头合同能否成为合同诈骗罪的形式要件题目,但实质上反映了构成合同诈骗罪的必备要件题目。
由于根据唯物辩证法关于形式与内容相同一的观点,形式是内容的内部组织,它把内容的因素连在一起,没有形式,内容本身就不存在。
[7]因此,形式题目在某种程度,某种意义上讲反映了实质题目,即内容所反映的实质需通过形式来体现。
所以,《刑法》用法条形式形成规范以惩办犯罪行为,体现了立法机关所要保护的社会客体的本质内容。
故而,探讨合同诈骗罪客观方面的形式要件,可认为我们在司法实践中准确掌握合同诈骗罪的构成要件并与普通诈骗罪相区别找到一条简便,易行的切进点。
一,《刑法》第244条的立法本意应理解为书面合同 从《刑法》修订的历史背景望,当时在民商法上正施行原《经济合同法》,《技术合同法》和 《涉外经济合同法》,为了划清困扰司法界利用经济合同入行诈骗与经济合同纠纷的界线,维护经济合同治理秩序,立法机关在修订 《刑法》时特增设了合同诈骗罪。
因此,该三部合同法中有关合同成立的划定,必然成为立法机关着眼增设合同诈骗罪的基点。
原 《经济合同法》第3条划定“经济合同,除即时结清者外,应当采用书面形式”。
《技术合同法》第9条划定“技术合同的订立,变更和解除采用书面形式”。
《涉外经济合同法》第7条划定 “当事人就合同条款达成书面协议并签字,即为合同成立。
通过信件,电报,电传达成协议,一方当事人要求签订确认书的,签订确认书时,方为合同成立。
”该三部合同法无一例外埠都夸大经济,技术合同应当采用书面形式,据此作出立法机关将合同诈骗罪的形式要件定位于书面合同的理解不是没有依据的。
从文理解释上讲,《刑法》第224 条划定合同诈骗罪的诈骗行为发生在“签订,履行过程中”。
这里的“签订”一词,有论者主张即为“订立”,是指订约当事人之间就合同条款入行协商,双方意思表示一致而达成协议。
[8]文理解释的要旨是对法律条文的字义入行解释。
在《现代汉语字典》中,将“签订”诠注为“订立条约或协定并签字”;[9]将“订立”注解为“双方或几方经由协商,用书面形式 (把要约,合同)肯定下来”。
[10]什么样的合同需要 “签字”?那当然是具有可视的有形表现形式的书面合同。
因此,从字面词义上讲,“签订”与 “订立”,本为同义或相类似的含义,都是指书面形式的合同。
但因为《合同法》第10条划定“当事人订立合同,有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将“订立”一词扩张解释到可以用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肯定下来的含义,故而 《合同法》第10条所称的“订立”与《刑法》第224条所称的“签订”是有所区别的,并不能作相同或相类似的理解。
从这一角度可以望出,立法机关如斯区别的本意也是显著的,即合同诈骗罪的 “合同”在内容上是指以体现交易内容的经济合同,在形式上应指书面合同;而《合同法》划定的“合同”从内容到形式较为宽泛,不受此限。
任何合同的订立都是以合同的履行为目的的,但合同的履行必然以合同的订立为前置前提,即没有前面的订立合同,谈何后面的履行合同?在《合同法》中,订立合同后不予履行,将承担违约的民事责任;而在《刑法》中,合同诈骗罪在主观方面属目的犯外,在客观方面属数额犯,即行骗人必需实际据有被害人数额较大的财物才能构成犯罪,承担刑事责任。
换言之,假如行骗人只是与被害人签订了合同,而被害人未将财物交付给行骗人,即在合同尚未履行的情况下,行骗人不构成合同诈骗罪。
这说明《刑法》第224条中的“签订”和“履行”并非简朴,可以各自为阵的并列关系。
实际上这里的“签订”合同,主要是指行骗人利用此阶段实施了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行为,为后面在“履行”合同过程中非法据有被害人的财物创造前提,故本法条中的 “签订”与“履行”之间,主要是体现相互联结,依存,且具有先后顺序的关系。
因而那种将本法条中原本为同一体的“签订”合同和“履行”合同完全割裂开来分析对待的做法,违背了矛盾的统一性。
二,合同诈骗罪与普通诈骗罪各有特征 从论理解释的角度分析,书面合同在形式上是与口头合同相对应的。
所谓书面合同是指当事人双方订立的可以有形地表现所载各自权利义务内容的协议,其特点是有形性,可见性。
所谓口头合同是指当事人双方就各自的权利义务直接用语言达成的协议,其特点是无形性,不可见性。
如前所述,合同无论用何种形式订立都是以履行为目的的,书面合同和口头合同也不例外。
两者比拟,书面合同信仰“先小人后正人”的原则,将双方各自的权利义务通过有形的载体明确下来,便于即时或者日后履行;而口头合同的履行则完全基于双方的信用。
显然,口头合同是最具信费用的合同,其所体现的老实信用原则最能体现人类文明高层次的境界,并被整个社会所推崇,亦是订立合同的要旨。
比拟而言书面合同的信费用差之。
但口头合同有其最致命的弱点就是与市场经济的现实不相吻合,去去因为缺乏证实力,给合同的履行造成严峻的障碍,这种障碍不仅会存在于口头商定阶段,也会存在于履行阶段。
而书面合同则无此之忧,即便发生争议也可凭其特有的证实力通过诉讼补救,这也体现出书面合同与市场经济的现实和要求是合拍的。
基于此,立法机关为了保护能够体现市场经济秩序的合同轨制,在修订《刑法》时特增设了保护经济合同轨制的合同诈骗罪。
毋庸讳言,合同诈骗罪是从普通诈骗罪中分解出来的罪名。
绝管两者之间本质上都是以非法据有为目的诈骗他人的财物,皆有虚构事实,隐瞒真相之共性,但两者除在犯罪主体上存在区别外,主要还有性质的差异: 第一,两者侵犯的客体不同。
普通诈骗罪侵犯的客体只是公私财物所有权之单一客体;而合同诈骗罪侵犯的客体是复杂客体,即为经济合同治理秩序和公私财物的所有权。
从《刑法》分则将合同诈骗罪回进第3章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之“扰乱市场秩序罪” 中,可以望出该罪侵犯的同类客体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主要客体仍是经济合同治理秩序。
第二,两者罪名的轻重不同。
比较《刑法》第224条和266条的划定,两者的法定最高刑一样,都可以判处无期徒刑;但两者的法定最低刑不同,合同诈骗罪最低只能判处拘役,而普通诈骗罪最低则可以判处管制,这说明前者重于后者,危害性也大于后者。
这也与合同诈骗罪中被骗取的财物数额较大的现实相吻合,而普通诈骗罪中行骗人利用口头合同诈财则不可能达到如斯的危害后果。
第三,两者客观方面不同。
合同诈骗罪的诈骗行为发生在签订,履行合同的特定时段,且在合同的内容上主要是指体现市场秩序的经济合同。
在形式要件上,如前所述应当是书面合同;而普通诈骗罪则无此时段和内容的限制,在形式要件上表现为口头合同。
第四,两者存在一般性与特殊性的关系。
普通诈骗罪是诈骗犯罪的基本形态,具有一般性;而合同诈骗罪是诈骗犯罪的特殊形态,具有特殊性,即两者属于法条竞合关系。
根据刑法理论上特别法条优于普通法条的原则,行骗人的诈骗行为如未触犯特别法条的划定,应以普通诈骗罪处断,只有行骗人的诈骗行为触犯了 《刑法》第224条之特别法条的划定,才应以合同诈骗罪处断。
众所周知,在普通诈骗罪中,大凡行骗人去去是以各种甜言蜜语来与被害人达成所谓的商定(协议),从而骗取对方的财物。
按《合同法》的划定,这些都应是口头合同,对此种口头合同如皆以合同诈骗罪处断,则立法机关在修订 《刑法》时似无保存普通诈骗罪之必要,或者亦无增设合同诈骗罪之必要。
合同的履行可以在订立时即时履行,也可以商定在订立后的某段时间内履行。
故无论行骗人是在订立仍是在履行口头合同过程中骗取财物,如都以合同诈骗罪论处,皆存此难解之题。
所以,以为口头合同可以成为合同诈骗罪形式要件的观点有违立法本意。
据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立法机关在 《刑法》中同时确立合同诈骗罪和普通诈骗罪,表明两者在形式要件上必有其各自的特点,书面合同应是合同诈骗罪的特有特征,而口头合同才是普通诈骗罪的特有特征。
这一结论的得出可为我们区分两者找到一个利便之门。
三,《合同法》的制定并不影响,改变合同诈骗罪的形式要件主张扩张说者自有其理论和法律依据,即以 《合同法》有关对合同形式的划定为底本。
而主张有限扩张说者之所以不愿将口头合同排除在合同诈骗罪的形式要件之外,不过乎是因为被《合同法》有关合同订立的划定所羁绊。
所以,探讨《合同法》的制定对 《刑法》中合同诈骗罪的形式要件的改变,影响与否实有必要。
也许主张扩张说或者有限扩张说者可能会以为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本身具有前瞻性,即除了留意已然性外,还会留意到未然性,且从原 《经济合同法》,《技术合同法》,《涉外经济合同法》三部合同法中确立的在经济,技术合同的基础上,扩张为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一节,说明立法机关在修订《刑法》时,已留意到将来制定的同一 《合同法》有关合同形式的内容,并以 《合同法》的制定晚于《刑法》的修订,以后法的效力优于前法的规则为由,入而得出《合同法》有关对合同形式的划定理所当然地应当成为理解《刑法》中合同诈骗罪相关题目的结论。
依其一,立法机关在制定,修改法律时确实是具有前瞻性的,但因为受立法思惟,理念,客观现实等诸多因素的局限,其所制定,修改的法律缺乏前瞻性的情况并不鲜见。
就以《刑法》为例,该刑事立法当初被理论界称为建国以来一部同一,完备的刑法典。
[11]但从1997年修订并施行以来,因为东南亚金融危机,“9.11事件”等国际事变和海内泛起了违背会计法划定,扰乱期货市场,破坏森林资源等犯罪流动,立法机关于1998年12月至 2002年12月,在短短的5年时间里,先后制定了 《关于惩办骗购外汇,逃汇和非法买卖外汇犯罪的决定》的单行刑法,并对1997年《刑法》入行了4次修改。
这五次对《刑法》的重大增补,修改,有些是由于社会糊口泛起了新的变化而为之,有些只能说立法机关原来在修订 《刑法》时存在考虑不周全的题目所致,因而可以说立法机关于1997年修订 《刑法》时,对未然性方面的预见力不够,以致该部刑法典的前瞻性有所欠缺已是不争的事实。
这正说明遵循罪刑法定原则的刑法,对严峻危害社会糊口行为的规范,亦只能永遥起到“事后诸葛亮”式的惩戒作用。
其二,《合同法》属于民商法这一部分法中债法的一个门类,其虽与《刑法》都是我国法律体系中的组成部门,但两者之间各自调整的社会关系的性质显有不同。
《合同法》调整的是同等主体之间财产关系中某一方面的详细题目;而《刑法》则是独立的部分法,与民商法,行政法等其他部分法一样都是基本法律,其调整的社会关系的范围比《合同法》等其他部分法更广,是强制力最大,惩办手段最为严肃的法律,也是维护,执行其他部分法的坚强后盾。
应当说,《刑法》的划定与其他部分法的划定之间是互相衔接的,具有传承入而发生质变的关系,如: 《公司法》划定虚报注册资本骗取公司登记情节稍微的,由工商行政机关予以行政处罚;虚报注册资本数额巨大,后果严峻或者有其他严峻情节的,则被《刑法》吸收,构成虚报注册资本罪。
换言之,在其他部分法的强制力不足以处罚违法者的违法行为时,则需要制定 《刑法》予以规范,惩罚,以保护人民,维护社会秩序。
但是,其他部分法所调整,保护的社会关系的内容业经 《刑法》确立,则对 《刑法》的合用,解释和理解,必需依罪刑法定原则,并按其独立的严格程序入行,而不能简朴地用其他部分法予以参照,理解,立法机关晚于《刑法》所制定的 《合同法》也不例外,其所划定的合同成立的形式,并不能改变,影响《刑法》中对合同诈骗罪的形式要件的界定。
由于《合同法》对《刑法》的合用不产生溯及力。
所以,书面合同也只能是 《刑法》修订时被其确立为合同诈骗罪的形式要件。
况且,《合同法》第123条本身就划定“其他法律对合同另有划定的,依照其划定。
”这足以证实 《合同法》等其他部分法不是 《刑法》的特别法,两者之间不存在特别法与普通法的关系,也不存在因《合同法》的制定晚于《刑法》,其对合同形式所作划定的效力优于《刑法》相关内容的题目。
由于两者是性质,种别完全不同的两种法律,各自合用的对象是不同的。
综上所述,扩张说简朴地将民商事法律 《合同法》有关合同的划定,作为《刑法》中合同诈骗罪之“合同”参照,理解的法律依据的观点显然错误。
有限扩张说以为一般情况下书面合同是合同诈骗罪的形式要件的观点,有其公道的可取之处,但其对泛起特殊情况时不愿排除口头合同,将会因在司法实践中难以形成同一尺度,轻易造成混乱,为扩张说的主张找到理论借口,不宜实际操纵,应当坚决排除。
限制说将书面合同确立为合同诈骗罪的形式要件,既与立法本意相符,也利于司法实践中划清两者之界线,使其一目了然,有利于司法实践的详细操纵,应当确立其应有的地位。
由于对合同诈骗罪的形式要件,《刑法》的构成要件肯定要严于《合同法》,故而应当严格限定于书面合同,从而摒弃口头合同可以成为合同诈骗罪形式要件的结论。